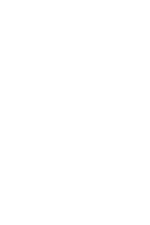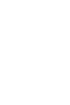《落葉》:生活還有甚麼值得期待
真不敢相信觀看《落葉》成了兩天以來最期待的事情,成了提前把工作完成的原因。對電影抱有期待是件危險的事,一方面在觀看的時候身體變得僵硬,另一方面好像在說明在原本的生活裡無甚麼能夠期待,在生活裡無甚麼能夠期待是危險的。觀看電影在某情況下可以說是毫無意義、毫不重要,而電影對生活本身的影響也沒有想像中的大,它卻在以不可見的方式影響我們做事的方法。坐在電影院看電影,一時恍神我就會覺得這回事是由金錢換來的,一種特殊的人類體驗,只為特定的人群開放,並不如想像中般屬於大眾。
我們談到電影,每人指向的、想像中的、愛看的電影都不同;可是看電影這回事,無論如何定義,還是類似的。胡晴舫寫了篇文章叫《美好》:「我的頭髮正一根根地發白,我的電腦裡還有一堆工作。可是,我還能從從容容吃頓像樣的晚飯,也許趕場電影。在午夜之前,我都還可以忘掉自己。」安妮艾諾寫了本關於真誠的小書《只是戀情》:「已經是四月了。我常常在清晨睡醒後並沒有立即想到A。約朋友聊天、看看電影、吃頓好飯,生活中畢竟還有小小的樂趣,因而未來的日子已慢慢顯得並不十分難熬了。」
對,已經是四月了。這一星期看的兩部芬蘭電影,都把時間搬到了台詞裡,我是由衷地感謝他們。(尤其《聖誕不快樂》提醒我,我還能完全掌控一天之內的八小時,我更願意拿起書本不放手。)選擇在光影裡度過時間,也不代表我們要忘了時間、忘了現實。儘管《都市浪人》裡的女子在面對別人的姍姍來遲時,說了:「沒關係,時間不存在。」《落葉》的她到網吧借用手提電腦,半小時要付上十歐元,折騰過後付了八歐元,負責人把電腦交到她手上時,說:「一分鐘已經過去了。」
《落葉》成了一齣八十分鐘而不是八小時的電影,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每人在現實裡的時間有限,而電影和現實更是有著無法說明的關係。芬蘭導演和法國作家之間的連結可能不大,但他們描寫私人感情和現實世界的交會是相似的。雅基郭利斯馬基把在二零二四年近乎絕跡的收音機放到她家,播放的新聞圍繞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民眾當作避難所的劇院被摧毀。她把惱人的聲音關掉,在男和女的交談之間,只剩下家裡的時鐘滴答的響。透過後期製作和戲院音響,我們聽見聲音在走,而我發現我家裡已經沒有時鐘了。
安妮艾諾等待來電,寫著慾望,寫著私人的事情,寫著寫著突然寫到:「我能清晰地回憶起與A交往期間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如阿爾及利亞的十月暴亂、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月十四日的酷熱,甚至像與A相會前的那天買了一個切菜機那樣瑣碎的小事。儘管如此,我依然感到,我很難把我此刻的寫作同一場暴風雨或近五個月來世界上發生的任何事情——柏林圍牆的推倒或齊奧塞斯庫的處死——聯繫在一起。生活在戀情中或寫作中,一個人所感受的時間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活在尚未被戰爭波及的地方,還能看一場電影。或許我還能說,我真愛這些只拍一個人的single shot,在同樣的街景走向右走出去的女人、走向左走回來的男人,間中插入的工業場景,在《鄉村牧師日記》被提起的時候往狂喜方向走的笑意,毛髮亮麗的小狗,向人發問:「乘坐火車的乘客,身體的振動是演技嗎?」的時刻。
仍活著,或許還能因為《落葉》而去看《不法之徒》、《喪屍未逝》、五六七月的雅基郭利斯馬基電影節。看一場電影,對世界不會帶來任何影響,可是許多無用的小事情堆砌起來成了人的一生,如同許多無用的小物件構成了家。私密書寫、體驗愛的重要性超出想像;在僅存的日子裡體驗甚麼,去愛,成了我們唯一能做的事。
期待藝術,創造藝術,成了生存的補償。那就先跑出去再說吧?提及到時間的兩位芬蘭導演,結束電影的方式也同樣:往世界的方向走。
奈良美智這年六十四歲,他在訪問裡總結了一些體會:「我的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都跟藝術沒有關係。我想其實每個人也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我自己因為做了這麼久的藝術工作,真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狹小的世界,從事藝術的人很容易就互相認識,但我認為藝術以外的世界其實更大更寬廣,如果只知道藝術、只懂藝術,那是非常可惜的。我希望大家知道,藝術之外,世界非常大。這是我從事藝術創作這麼久以來,總算體會到的道理。」